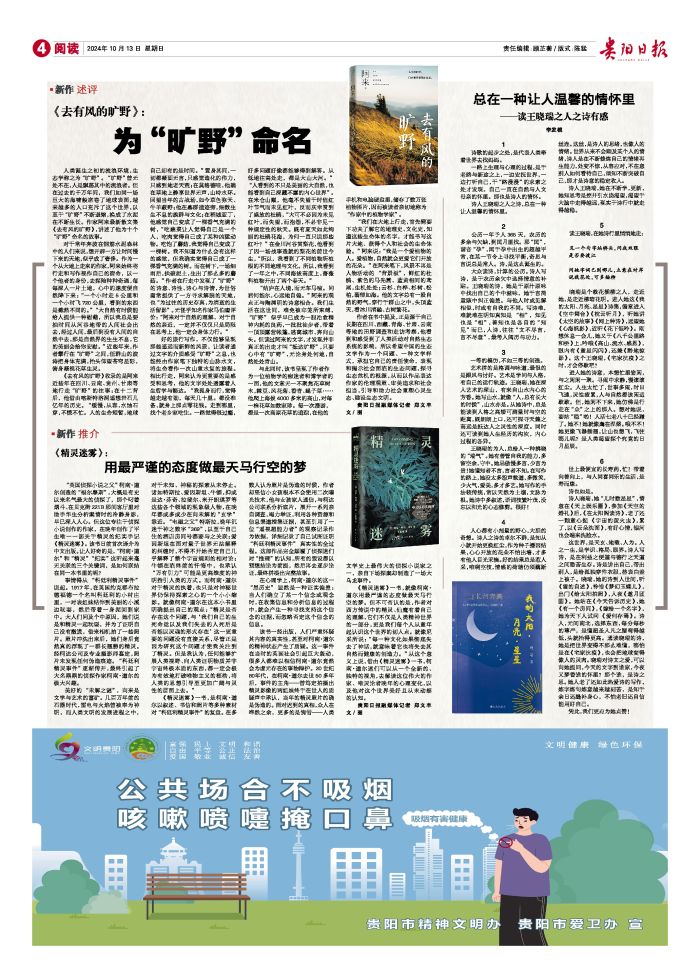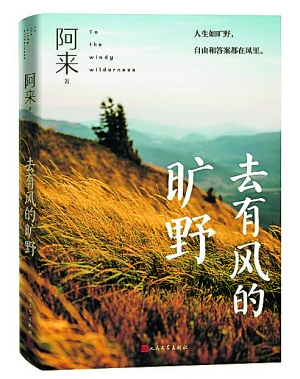
人类诞生之初的流浪环境,生态学称之为“旷野”。“旷野”曾无处不在,人是飘荡其中的流浪者。但在过去的千万年间,我们如同一场巨大的海啸般席卷了地球表面,越来越多的人口充斥了这个世界,以至于“旷野”不断退缩,换成了水泥在不断生长。作家阿来最新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讲述了他为十个“旷野”命名的故事。
对于常年奔波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人们来说,想开辟一方让时间慢下来的天地,似乎成了奢侈。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将行走和写作视作自己的宿命,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近些年来,作者攀行在“旷野”之间,任群山的波涛把身体充满,抬头仰望苍穹星际,俯身凝视花草生灵。
《去有风的旷野》收录的是阿来近些年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地行走“旷野”的往事:在十二背后,他借由喀斯特溶洞遥想岩石几亿年的历史。“缓慢,从容,水蚀石穿,不慌不忙。人的生命短暂,地球自己却有的是时间。”置身其间,一切都凝固无言,只感觉造化的伟力,只感到地老天荒;在莫格德哇,他躺在草地上静享世界无声,山峙水环。回望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他在墓群遗迹旁,细数生生不息的族群与文化;在稻城亚丁,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香气充满的树,“吃蔬菜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吃肉觉得自己成了某种凶猛动物。吃饱了蘑菇,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确实觉得自己成了一棵香气充满的树。而在树下,一场细雨后,拱破泥土,生出了那么多的蘑菇。”作者在行走中发现了“旷野”的诗意、诗性、诗心与诗情,为世俗庸常提供了一方寻求解脱的天地,也“为过往的历史存真,为消逝的生活留影”。无怪乎知名作家马伯庸评价:“阿来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自然的亲近,一定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思考上,他一定会身体力行。”
好的旅行写作,不仅能够呈现那些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也能经由作家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将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的文字处处透露着人生哲学与豁达。“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都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地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人看到的不只是美丽的大自然,也能看到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在米仓山巅,他毫不失望于时值红叶节气而未见红叶,反而庆幸赏到了盛放的杜鹃,“大可不必因为未见红叶,而失望,而抱怨,不必非见一种规定性的秋天。既有夏天如此绚丽的杜鹃花海,为何一直只说那些红叶?”在金川河谷赏梨花,他看到了因一场战事造就的梨花的前世今生,“所以,我看到了不同植物所植根的不同地理与文化。所以,我看到了一年之中,不同海拔高度上,蔷薇科植物开出了两个春天。”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阿来的观点正与陶渊明的诗意相合。我们生活在这世间,难免被牢笼所束缚,“旷野”似乎早已成为一服治愈精神内耗的良药,一批批徒步者,带着一顶顶露营帐篷,逃离城市、奔向山头。但读过阿来的文字,才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抵达旷野”,只要心中有“旷野”,无论身处何地,自然处处青山。
与此同时,该书呈现了作者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的一面,他的文章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棘豆、风花菊、香青、蝇子草……他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每一次漫游,都是一次高原花草的追踪,在他的手机和电脑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因而被读者亲切地称为“作家中的植物学家”。
“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阿来笔下,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鲜红的杜鹃、紫色的马先蒿、蓝黄相间的鸢尾,生机处处;云杉、白桦、杉树、松柏,蓊郁如海。他的文字总有一股自然的野气,穿行于群山之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古树繁花。
作者在书中提及,正是源于自己长期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田野调查和走访考察,他看到和感受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所以希望中国的生态文学作为一个问题、一种文学样式,承担它自己的责任使命,表现和揭示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以作品表达作家的伦理观照、审美追求和社会担当,引导和助力社会重塑心灵生态、建设生态文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为“旷野”命名》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