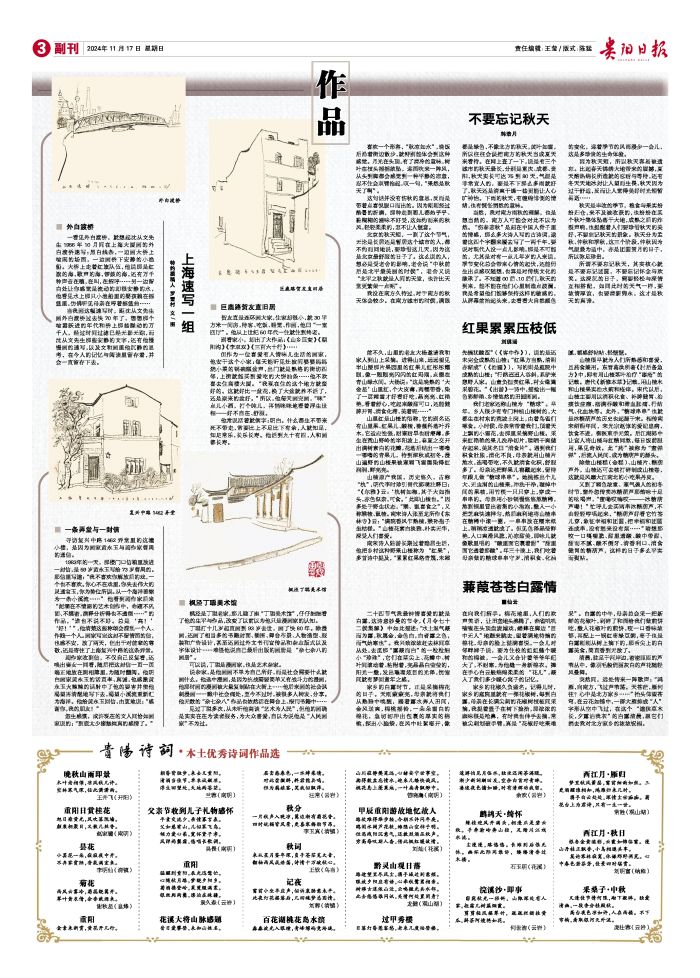刘琪瑞
前不久,山里的老友大杨邀请我和家人到山上采摘。进得山来,远远望见半山腰那片果园里的红果儿红彤彤耀眼,像一颗颗亮闪闪的红玛瑙,点缀在青山绿水间。大杨说:“这是晚熟的‘大金星’山里红,个大皮薄,肉糯带香,染了一层霜雪才好看好吃,晶亮亮、红艳艳,看着舒心,吃起来酸甜可口,还能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美着呢……”
山里红是山楂的俗称,它的别名还有山里果、红果儿、酸楂,蔷薇科落叶乔木,它适应性强,耐寒耐旱也耐瘠薄,多生在荒山野岭的半阳坡上,春夏之交开出满树素白的花瓣,花落后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青果儿,待到深秋或初冬,漫山遍野的山楂果被寒霜飞雪濡染得红润润、鲜亮亮。
山楂原产我国,历史悠久,古称“朹”,明代李时珍引晋代郭璞注释曰:“《尔雅》云:‘朹树如梅,其子大如指头,赤色似柰,可食。’此即山楂也。”因多处于野生状态,“猴、鼠喜食之”,又称猴楂、鼠楂。南宋诗人张至龙所作《东林寺》云:“满院香风乍熟楂,猴孙抱子坐枯槎。”山楂花素白淡雅、朴实无华,深受人们喜爱。
南宋诗人陆游长期过着隐居生活,他把乡村这种野果山楂称为“红果”,多首诗中提及,“累累红果络青篾,未霜先摘犹酸涩”(《客中作》),说的是还未完全成熟的山楂;“红果方当熟,清阴亦渐成”(《治圃》),写的则是庭院中成熟的山楂;“行路迢迢入谷斜,系驴来憩野人家。山童负担卖红果,村女缘篱采碧花。”《出游》一诗中,描绘出一幅色彩鲜艳、乡情悠然的田园图画。
我们老家还称山楂为“糖球”。早年,乡人很少有专门种植山楂树的,大都生在村东的荒坡土岗上,由着鸟雀们啄食。小时候,母亲常带着我们,顶着天上飘的小雪花,去那里采摘野山楂。采来红艳艳的果儿洗净切片,晾晒干爽储存起来,美其名曰“消食片”。遇到我们积食肚胀,消化不良,母亲就用山楂片熬水,连喝带吃,不久就消食化积,舒服多了。母亲还把鲜果儿窖藏起来,留待年跟儿做“糖球串串”。她挑拣出个儿大、无虫洞的山楂果,冲洗干净,璇掉中间的果核,用竹筷一只只穿上,穿成一串串的。母亲用小砂锅慢悠悠熬糖稀,熬到锅里冒出密集的小泡泡,撒入一小把芝麻快速拌匀,然后麻利地将山楂串在糖稀中滚一圈,一串串放在糯米纸上,稍稍凉透就成了。但见色泽晶莹鲜艳,入口爽滑风脆,沁凉甜美,那味儿就像歌里唱的“酸里面它裹着甜”“甜里面它透着那酸”。年三十晚上,我们吃着母亲做的糖球串串守岁,消积食、化油腻,顿感舒帖帖、轻惬惬。
山楂很早就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且药食兼用。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即有用山楂茎叶治疗“漆疮”的记载。唐代《新修本草》记载,用山楂木和山楂果实治水痢和疮痒。宋代以后,山楂主要用以消积化食、补脾健胃、治痰饮症瘕、痞满吞酸和滞血胀痛、行结气、化血块等。此外,“糖球串串”也就是冰糖葫芦的历史也起源于宋。相传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赵惇的爱妃患病,饮食不进,御医束手无策。后江湖郎中让宫人将山楂与红糖同熬,每日饭前服用,果见奇效。此“药”被称为“蜜弹弹”,后流入民间,成为糖葫芦的源头。
除做山楂糕(金糕)、山楂片、糖葫芦外,山楂还可去核打碎制成山楂卷,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的小吃果丹皮。
又到了霜色浓重、寒气袭人的初冬时节,窗外忽传卖冰糖葫芦那韵味十足的吆喝声,“蜜嘞哎嗨哎———冰糖葫芦嘞!”忙呼儿去买两串冰糖葫芦,不由轻轻哼唱起来,“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暗想那咬一口嘎嘣脆、甜里透酸、酸中带甜、甜而不腻、酸不倒牙、清香利口、消食健胃的糖葫芦,这样的日子多么平实而熨帖。
(《红果累累压枝低》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