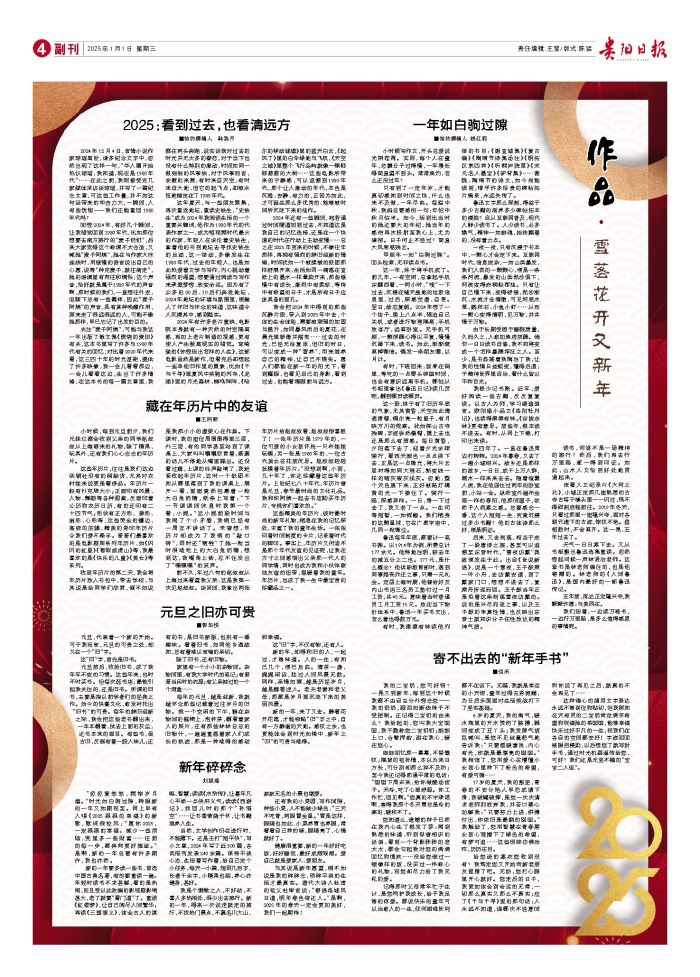■特约撰稿人 钱红莉
小时候写作文,开头总爱说光阴荏苒。实则,每个人在童年,总嫌日子过得慢,一年漫长得简直望不到头。常常焦灼,怎么还没过年?
只有到了一定年岁,才能真切感知到时间之快,什么也来不及做,一年尽矣。每临中秋,我妈总要感伤一句:年怕中秋月怕半。如今,活到比当时的她还要大的年纪,她当年的感伤再次投射至我心上,尤为痛彻。日子何止不经过?简直大风席卷残云。
甲辰年一如“白驹过隙”。回头检索,无非读点书。
这一年,终于将手机戒了。前几年,一有空闲,总拿起手机东翻西看,一两小时,“嗖”一下过去,沉浸在铺天盖地的垃圾信息里,过后,深感空虚、自责。翌日,故态复萌。2024年想了一个法子,晚上八点半,强迫自己关机,或者进行物理隔离,手机放客厅,远离卧室。无手机可刷,一颗浮躁心得以平复,慢慢沉潜下来,读书。如此,渐渐疏离掉微信。偶发一条朋友圈,以月计。
有时,下班回来,饭煮在锅里,等吃的一点零头碎脑时间,也会有意识远离手机。哪怕从书柜里拿出《鲁迅日记》读几页呢,翻到哪页读哪页。
这一段,终于有了旧历年底的气象,尤其黄昏,天空如此清透肃穆,偶尔亮一粒星子,有月映万川的荒寒。犹如深山古寺残碑,字迹纵然模糊,摸上去也还是那么有质感。每日黄昏,夕阳落下去了,迎着夕光余晖骑行,看西天颜色一点点淡下去,正是这一点微光,将大片云层衬得如同大理石,渐变线一样的暗灰银灰浅灰。忽地,整个天色黑下来,正好被路灯橘黄的光一下接住了。骑行一路,深感异样。一日,滑一下过去了,我又老了一点。一生何等短暂,一如蜉蝣。我们栖身的这颗星球,它在广袤宇宙中,几同一粒微尘。
鲁迅每年年底,都要计一笔书账。以1914年为例,所费总计177余元。他特地注明,较去年约减五分之二也。177元,是什么概念?他供职教育部时,遇到同事婚丧乔迁之事,只需一元礼金。定居上海时期,他曾给好友内山书店三名员工垫付过一月工资,共45元。意味着当时普通员工月工资15元。放在当下物价体系中,鲁迅一年买书支出,怎么着也得数万元。
有时,我津津有味读他列举的书目:《谢宣城集》《复古编》《陶靖节诗集汤注》《明拓汉隶四种》《听桐庐残草》《宋元名人墨宝》《驴背集》……谢眺、陶靖节的诗文,如今尚能读到,惜乎许多珍贵的碑帖拓片辑录,永远失传了。
鲁迅文字那么深刻,得益于多少古籍的滋养多少碑帖拓本的浸染?自从互联网普及,现代人鲜少读书了。人少读书,必多燥气,精神一如游魂,始终飘着的,没有着力点。
一夜一夜,只有沉浸于书本中,一颗心才会定下来。互联网时代,信息庞杂,一如山洪暴发,我们人类的一颗颗心,便是一条条河流,暴发的山洪泥沙俱下,河流变得赤铜般浑浊。只有让自己慢下来,变得舒缓,泥沙渐沉,水流才会清澈,可见河底水草、鹅卵石、小鱼小虾……从而一颗心变得清明,见万物,并共情于万物。
由于长期受困于睡眠质量,久而久之,人愈加焦虑烦躁。倘非一日日读书自修,我不知将变成一个怎样暴躁浮泛之人。至少,是书涤荡着我陶冶了我,让我的性情日益蜕变,懂得后退,于精神世界里自治,看什么皆以平和目光。
我极少记书账。近年,爱好阅读一些古籍,反反复复读。以古人为师,学习锻造语言。欧阳修小品文《洛阳牡丹记》,也读得津津有味。《东坡志林》更有意思。前些年,根本读不进去。有时,从网上下载,打印出来读。
三四年了。一直在鲁迅周边打转转。2024年暮春,又去了一趟小城绍兴。故乡还是那样的故乡,一日日,成千上万人群,潮水一样来来去去。随着喧嚣人流,我在他居住过两年的卧室前,小站一会。纵然室外遍布金箔一样的春阳,他那间屋子,依然予人烈寒之感。总要感念一番,这个人短短一生,究竟沉浸过多少书籍?他的古体诗那么好,便是明证。
后来,又去剡溪,相当于走了一段唐诗之旅,甚至可以追溯至东晋时代,“雪夜访戴”典故便发生于此。出自《世说新语》,说是一个雪夜,王子猷乘一叶小舟,去访戴安道,到了戴家门口,想想不进去了,复乘舟折返而回。王子猷当年正是沿着这条剡溪雪夜访戴的。说的是兴尽而返之事,以及王子猷的率真性情,也反映出东晋士族知识分子任性放达的精神气质。
读书,何尝不是一场精神的旅行?然后,我们再去行万里路,逐一得到印证。如此,山水人文恰到好处地贯通起来。
夜看人文纪录片《大河之北》,小城正定那几座熟悉的古寺古塔于镜头里一一闪过,恨不得即刻启程前往。2019年冬天,只看过那里一座隆兴寺,面对各朝代遗下的古迹,惊叹不绝。盘桓数时,不舍离开。这一晃,五年过去了。
天气一日日寒下去。又从书柜搬出鲁迅选集重读。忽然想起问候一声林贤治老师。这套书是林老师编注的,也是他寄赠的。林老师的《人间鲁迅》,是国内最好的一部鲁迅传记。
五年前,抵达正定隆兴寺,我默默许愿:与美同在。
我们活着,一边读万卷书,一边行万里路,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情呢。
(《一年如白驹过隙》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