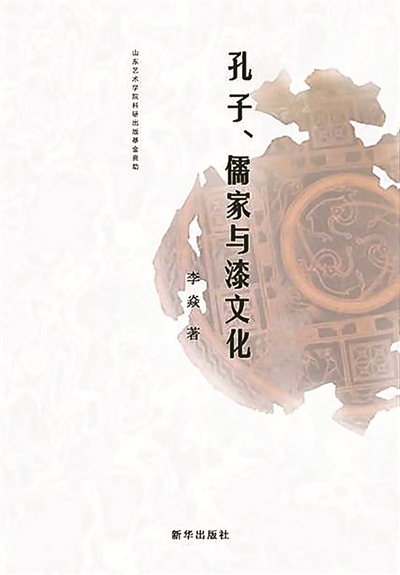
通常认为,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李焱著 《孔子、儒家与漆文化》一书将“漆”的作用等同于笔墨纸砚,认为“漆”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亦是中华文化本质的显性形态。
历史地看,“漆”先作为涂料使用,后用于记载文字及建筑、绘画、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原始部落就发现了生漆的痕迹,这些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生漆采集和髹涂技术;商代的漆艺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薄片和宝石镶嵌等较复杂的工艺;春秋战国时期,漆树的分布十分广阔,已有大片人工种植漆林。漆园经济与桑麻盐铁相提并重,漆价弥贵,消费群体以王室贵族为主;秦汉时期的漆艺空前繁荣,出现了以宣扬义士、孝子、圣君、贤相等儒家思想题材的漆绘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廉价的瓷器兴起,漆器的使用受到影响,但漆器材质带来的豪华高贵及不可代替的独特性,使其渐渐成为颇具观赏性的艺术品,逐步脱离了实用范畴;明清时期是中国近代漆艺的高峰期,“福州脱胎漆器”“景德镇陶瓷”“北京景泰蓝”并称为中国工艺美术三宝。
该书的独特见解在于将基于“漆”的“漆艺”“漆文化”与孔孟儒家文化联系在一起。具体表现有三:一是漆与笔墨相比,其材质、色质更加温润而含蓄,内敛而深沉、高贵而不张扬,精神层面上特别符合儒家“温良恭俭让”精神标尺的诠释。就色彩及装饰纹样来看,亦体现了“礼治”教化的结果。在中国,颜色装饰从来都不是以还原客观为目的,而是有极强的寓意指向。对于色彩,孔子有“恶紫夺朱”之论,把红色作为正统的象征。自漆器成型,黑红两色便开始成为漆器的主色调,充满儒家“礼治”下优雅与大气的神韵;二是漆材料在创作和制作中的“异变”特性,增加了创作者把握的难度,显得更加神秘和变化万千。同时也显现出中国人“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世界观的最佳表现形式;三是“礼治”的具体物化形态之一。先秦时期的礼器有玉器、青铜器、漆器及服饰等。孔子对于包含漆器在内的礼器之尊崇是无以复加的,他认为上古淳朴的“礼治”之理想盛世,其物化的具体形式即为礼器,礼器承载了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运行。
对此,作者以山东日照海曲、临沂金银雀山出土的汉代漆器文物为例作说明,认为其形制、用料、设色、纹样,均以“礼”的规制来设置和摆放。从品类划分还是整体造型上,都可从漆器上看到青铜礼器的影子;其奁盒、耳杯、盘、壶,从形制到花纹,无不神似,几乎可看作青铜器的复刻品。漆器的整体造型也满是青铜器的味道,充满简约的元素,如直线形或几何形,带着青铜器的素朴大气,体现了创作者坚定的精神信念,显得规则而符合礼法,以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后的教化作用,其“中正仁和”之感与先秦楚地漆器中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风格迥异。
总之,作者认为,最早作为涂料使用的漆,在儒家思想成形之初,即具有文化载体的作用,可见诸于历代文献。漆作为载体,对于儒家思想的奠基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的确立、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漆密不可分。与之对应的是,以漆作为材料和手段,宣传、反映儒家思想的文艺作品(包括漆器、漆画和漆塑,以及古建筑的漆装饰),两千年来绵延不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