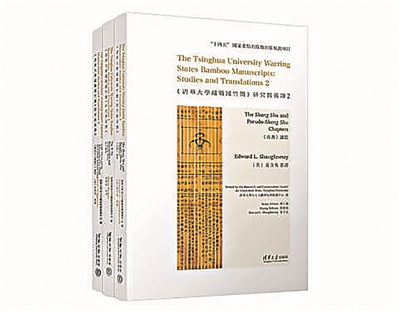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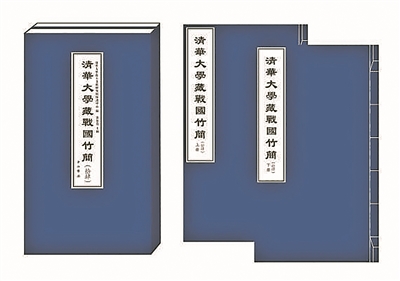
2024年年底,清华简公布了最新的第十四辑整理报告。

清洗整理后的清华简。

上世纪70年代,在沙滩红楼,李学勤(右一)参与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睡虎地秦简等多批简帛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

清华简初期整理研究团队,更像一个临时的课题组。
杨丽娟
2006年,一批两千多年前的竹简在香港神秘现身。然而,扑朔迷离的身世,假简横行的市场,让它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历经波折之时,这批司马迁也没看过的典籍,幸运地遇到了“国宝级”学者李学勤。
千年竹简入藏百年清华,冥冥之中找到了最好的归宿。2500枚逃过秦火的历史“碎片”得以复原,随着十四辑整理报告陆续公布,清华简颠覆的历史越来越多:忠臣表率周文王竟早有灭商之心?烽火戏诸侯根本不存在?“卧薪尝胆”另有新解……
曾经的“冷门绝学”被看见,然而,对于“简帛圈”外的大众而言,“高大上”的清华简何以震撼?它重现了多少古书,重建了哪些古史?很多人可能不甚了了,甚至面对网络上所谓的清华简“真伪之争”人云亦云。
今年4月,清华简将再次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最晚到明年,清华简的全部整理工作也将完成。走近清华简,还有很多值得讲述的新故事。
传奇
司马迁也没见过的典籍
清华简的入藏,缘于一次“大佬的饭局”。在《清华简与古代文明》的课堂上,每每说起清华简的传奇身世,授课老师程浩总会讲起这个故事。
2008年6月的一天,为欢迎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到校任教,清华大学校领导出面宴请,并特邀杨振宁夫妇和李学勤夫妇作陪。杨振宁作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自然无需多言。李学勤早年就读于清华,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用当下流行的说法,他堪称一位“六边形战士”,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领域都造诣深厚。
宾主畅谈之时,李学勤提到了一件事:曾有人在香港见到一批流散的竹简,尽管内容和年代尚不详,但可能有重要价值。校领导问:“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话概括一下这批竹简的意义?”李学勤回答:“如果是真的,那就是连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
校领导闻言,顿觉此事重大,当机立断——竹简真伪,由李学勤来调查,是否购买,由学校来决策。
其实,在此之前,李学勤已经听闻这批竹简的消息。同样是在一个饭局上,不过这次做东的是李学勤,客人则是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张光裕。在清华大学熙春园,两位老友边吃边谈,张光裕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继上博简后,香港又发现了秦、楚竹书。
张光裕口中的“上博简”,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批竹简的回归,正是得益于他的敏锐与推动。1994年,在香港古玩市场,张光裕偶然见到浸泡在泥浆与浊水中的竹简时,一眼认出上面的楚文字“周公曰”。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一边不动声色地与古玩商周旋,摹写、考辨竹简内容,一边迅速联系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最终,成就了一桩文物抢救与回归的美谈。
时隔十多年,香港市场再现珍贵竹书,不能不令人激动。但竹简的具体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直到2006年年底,神秘的竹简才初露真容。彼时,200余位学者齐聚香港,为庆祝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一众老先生中,时年37岁的刘国忠还是青年一辈。他对那次研讨会最深的印象是,“规模太大了,大得合影都不好拍,只能分批一拨一拨跟饶先生合影。”事后,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热闹的会议间隙,还有一件即将影响海内外学术界的大事正在发生——张光裕带着几位老友,悄悄去看了那批神秘竹简。这其中,就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陈松长教授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均明研究员。
不看不知道,原来神秘的竹简竟有两批:一批楚简,一批秦简。面对珍贵的竹简实物,两位老先生既感到心痛,又难掩激动。经多方努力,岳麓书院成功购回了价格相对较低的秦简,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岳麓秦简。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本有意收购楚简,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于是,这批竹简只能继续流散于市场,处境岌岌可危。
普通读者可能意识不到竹简的脆弱性。竹简一旦出土,如果没有加以科学保护,很快就会滋生霉菌,这些霉菌甚至可能彻底毁掉保存了两千年的竹简。事实上,陈松长曾在访谈中披露,岳麓秦简被购回前,“简牍上已经有霉斑的痕迹,状况很不乐观”。
幸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危在旦夕的竹简遇到了“国宝级”学者李学勤。在为岳麓秦简担任专家鉴定组组长时,岳麓书院的老师告诉他,香港古董商手中还有另外一批战国简。联想到当年张光裕在熙春园所说,李学勤几乎凭着直觉意识到,这批竹简非同寻常。
然而,竹简毕竟是因盗掘而重见天日,具体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已无从考证。况且,彼时的香港文物市场假简横行,谁也不敢贸然出手购买这么大一批竹简。即便是李学勤,也必须慎之又慎。
2008年6月,得到校领导委托的第二天,他找到了学术圈内流传的8支样简照片。8支简全部由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书写,其中一支简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仇”,在这里的读音念“qiú”,是晋文侯的名字。这个字的楚文字字形很特别,没有深入研究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写法。刘国忠是李学勤的弟子,自2008年起,一直跟随老师研究清华简,如今已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他解释说:“这支简说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两周之际,惠王被晋文侯仇杀于虢国。这一事件只在已经失传的古本《竹书纪年》中有过记载,《史记》等其他古籍根本没有提及。”
一个生僻的楚字,一段失传的古史,都在告诉李学勤,这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战国竹简。
事不宜迟,7月9日,李学勤专门去了一趟香港。稳妥起见,他特邀李均明研究员同行,然后在张光裕的陪同下,一起去观摩竹简实物。三位大咖意见一致,但为确保万无一失,清华还是与古董商特别约定:先把竹简交给清华,待确认全部为真之后,再付款购买;如果是假,清华可以把竹简退回,不必付款。
一个星期后的7月15日,正值酷暑难耐的夏日,中午1点,刘国忠跟随老师李学勤在清华图书馆老馆静静等待。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批竹简终于从香港远道而来——它们先是搭乘飞机,后又转乘专车,风尘仆仆地抵达清华。从那一刻起,这批历经波折的无名竹简拥有了一个显赫的名字——清华简。
惊险
半天时间就能烂个小洞
清华简入藏那天,暑假已经开始,老师们原本打算先对竹简进行基本维护,等到秋季开学再正式清洗整理。
7月16日,刘国忠去检查竹简,一切看上去还算正常,与刚到时没什么区别。然而,到了17日,他只看了一眼,就“感觉有点不太好”——竹简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状物似乎变多了,而且颜色变得更白。他立刻打电话给李学勤,并向学校汇报。
清华的效率相当高,当天就安排实验人员,提取、检测浸泡竹简的液体。果然,白色粉状物就是活体霉菌。为什么竹简这么快就出现了霉菌?原来,这批竹简属于湿简,出土后必须保持湿润状态。为此,古董商将竹简连同湿泥用保鲜膜层层包裹,浸泡在了化学溶液中。
在地下水里泡了2000多年的竹简是什么样子?刘国忠打了个比方:“就跟开水里煮过的面条一样,软绵绵的,稍微碰一下就断了、碎了。”古董商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要兜售竹简,就得向人展示。于是,他们自作聪明地在一些竹简下面垫上新鲜竹片,再拿保鲜膜一裹,两头缠上透明胶带。殊不知,这些简单粗暴的“保护”措施,却让清华简陷入了更大的危险——未经杀菌的新鲜竹片,成了微生物滋生的温床。
“这太可怕了。”李学勤生前为学生讲课时,回忆初见清华简的情形,难掩心痛,“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半天时间,霉菌就能把竹简烂出个小洞!”
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一场团体作战迅速开始:去掉保鲜膜、去污、杀菌、重新浸泡……正值北京奥运会前夕,首都的安保工作前所未有地严格,偏偏清华简的抢救急需各种化学药品和器材,清华文科建设处的老师只能到处“刷脸”、找人帮忙。
竹简尺寸特殊,需要一些特别尺寸的托盘来盛放,什么样的托盘既环保、安全又耐用?情急之下,老师们灵机一动,从广东定做了一批类似食堂盛菜用的平底盘,只是尺寸稍有不同,总算解了燃眉之急。“文物保护工作经常这样就地取材。”在《清华简与古代文明》课堂上,看到熟悉的平底盘,同学们忍俊不禁,程浩老师笑着解释,“没办法,我们需要的器材量太小,经费又不多,没有厂家愿意批量生产。”
李学勤年事已高,眼睛不好,手也容易抖,直接上手“抢救”竹简的,除了最年轻的刘国忠,还有两位外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均明、赵桂芳夫妇。两位老师一个专注研究,一个侧重保护,两人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简牍,估计是全国最多的。唯独战国简,两人一直没机会参与整理。收到李学勤的邀请,这对刚刚退休的学术伉俪无缝衔接新工作,恨不得天天“长”在清华简的库房里。
整整三个月,李学勤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直奔清华图书馆老馆,了解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进展。在顶楼的一间弥漫着刺鼻化学气味的房间里,李均明、赵桂芳、刘国忠三人小组用最细最软的毛笔,轻轻除去竹简表面的污物。第一次跟着李均明老师学习除污,刘国忠戏称自己是“张飞绣花”,遇到顽固污物,一天只能清污一枚简。见多识广的李均明反倒一脸兴奋,“这不正好说明简是真的,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
当所有的抢救工作告一段落,紧绷许久的身心稍微放松,大家才感到一丝后怕:如果这些竹简再流散几个月,滋生的霉菌可能就会吞噬掉所有的竹简,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批无价之宝了。
疑案
旷世之争画上句号
与老师李学勤相比,第一次见到清华简的刘国忠,内心更多的是好奇。他研究过帛书,读过上博简,但见到触手可及的竹简实物,还是头一回。对于清华简中能发现什么内容,他起初有点将信将疑。然而,作为最早参与保护整理工作的成员之一,他很快体会到了老师内心的激动和震撼。
8月13日,李均明和刘国忠正在清洗竹简,一支简背上的四个字跃入眼帘——“尃敚之命”。竹简背面通常是没有字的,这四个字很可能是文章的篇题。这会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献呢?刘国忠赶紧打电话报告,闻讯赶来的李学勤一看,激动不已,当即认出竹简上的楚文字“尃敚”二字,就是“傅说(yuè)”。
傅说,商王武丁的贤臣,殷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读过有关他的故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与舜并列,被孟子视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励志榜样。
不过,身为历史学家的李学勤,看到这个名字,想到的却是一桩关于《尚书》的千古疑案。他说,《傅说之命》就是传世古文《尚书》中的《说命》。
众所周知,《尚书》是古代科举必读的四书五经之一,内容多为上古时代国君的文告,以及君臣的谈话记录等,堪称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相传,《尚书》是孔子编辑的。孔子周游列国,始终不得志,晚年干脆回到家乡,转型当了一个好编辑。他认认真真挑选了一百篇古代经典,整理成了百篇《尚书》。可惜,孔子精心编辑的经典问世之后,却命途多舛。
先是秦始皇焚书,民间私藏的《诗》《书》等都要交出来集中烧毁。幸好,一位名叫伏生的博士,把自己那套《尚书》偷偷藏了起来。秦末大乱,至西汉初年,伏生藏匿的百篇《尚书》只残留28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加以整理写定后,成了后人口中的“今文《尚书》”。
悄悄藏书的不只伏生。面对焚书令,孔子的后人想了一个妙计,他们把《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藏在了老宅的墙壁里。按说这样隐秘的地点应该天衣无缝,谁知遇到一个爱好营建宫室的奇葩邻居。这位邻居是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鲁恭王是个结巴,不善言辞,下令拆毁孔子老宅时却干脆利落。
被王国维誉为中国学问上三大发现之一的“孔壁中经”,就这样在鲁恭王“强拆”孔子故居时,重见天日。这批古籍用秦汉以前的文字书写,相比隶书,算是“古文”,因此被称为“古文《尚书》”。
令人唏嘘的是,意外现身的古文《尚书》,又在魏晋时期毁于战火。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通行《尚书》版本,源自东晋的一名官员梅赜。梅赜献给朝廷的这版《尚书》共有58篇,其中今文《尚书》33篇是对伏生的传本进行分合而成;而古文《尚书》25篇的来历就有点扑朔迷离了,据说源自孔壁中经。然而,究竟是真是假,自宋代以后,学问官司就没断过,就连朱熹也半信半疑。到了清代,古文《尚书》前已经被不少学者加上了一个“伪”字。
不过,质疑也好,辨伪也罢,学者们都是基于学理论证,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正因如此,重新发现一本早期《尚书》的写本,几乎成了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一种情结。古代史大家张政烺先生,就经常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什么时候能够挖出《尚书》就好了。
张政烺2005年辞世,他生前肯定想不到,仅仅三年后,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古文《尚书》,果真在清华简中被发现了。
原本的奢望在不经意间变成了现实,李学勤对《傅说之命》的解释,让大家都兴奋不已。刘国忠说,随后他们又陆续清洗出一些《傅说之命》篇的竹简,将竹简与传世的《国语》等先秦典籍相关引文对比,果然一字不差。
随着进一步释读,大家愈发欣喜,清华简《傅说之命》和梅赜古文《尚书》中的《说命》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讲了商王武丁依据天命寻找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后者却是傅说对武丁进言治国之道。
有意思的是,二者也有一些相似的话语,但说话的主语却不同。比如,《傅说之命》中有些傅说的话,在《说命》中却被安在了武丁头上。看来,“古人造假也不是凭空想象,很可能是根据传世的一些引文,加以扩充,编出了新文章。”刘国忠说。
当然,这样判断的前提是,清华简的确书写于战国时期。
2008年10月14日,在清华大学主楼的一间会议室,11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共同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鉴定组认为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
一个多月后,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出炉,与专家们的判定完全一致,竹简抄写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35年到公元前275年之间,相当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也就是孟子、庄子、屈原等先哲们生活的年代。
真伪已辨,一位清华校友个人出资,慷慨买下这批竹简,并无偿捐赠给学校。这样的结果也意味着,早于秦始皇焚书、失传2000余年的《尚书》,如今就在我们眼前。而一千多年来关于古文《尚书》的旷世之争也画上了句号,怎不令人欣喜异常?
(《惊世清华简》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