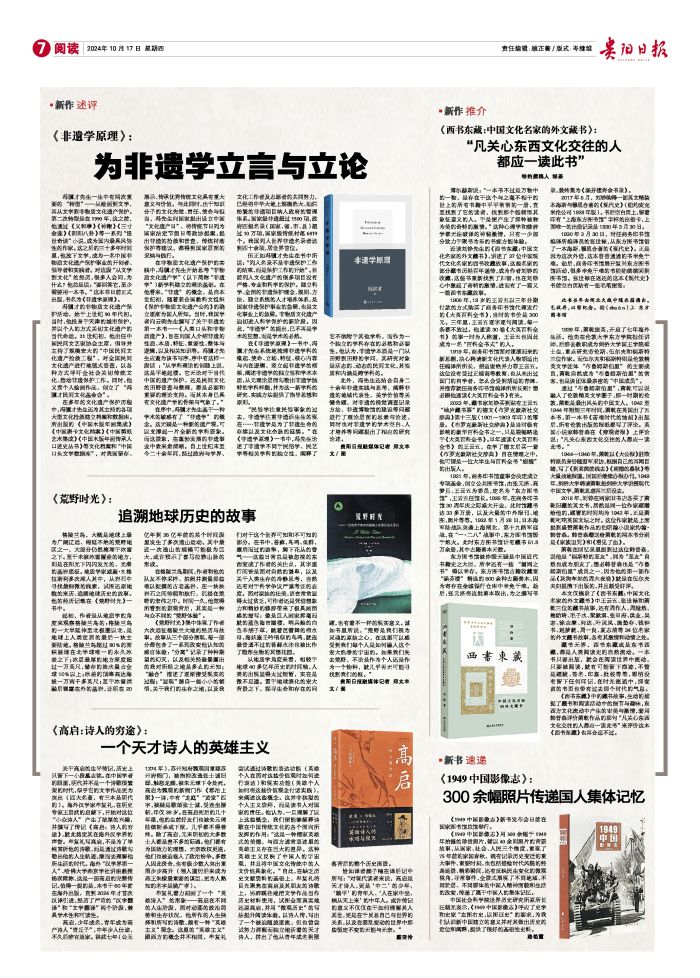冯骥才先生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型”——从绘画到文学,再从文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二次转型是在1990年,这之前,他通过《义和拳》《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一系列“怪世奇谈”小说,成为国内最具风俗性的作家。这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放下文学,成为一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创者、倡导者和实践者。对这段“从文学到文化”的经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他总是说:“要回答它,至少需要用一本书。”这本书日前正式出版,书名为《非遗学原理》。
冯骥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投身于天津的城市保护,并以个人的方式关切文化遗产的当代命运。21世纪初,他出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倡导并主持了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全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地毯式普查,以各种方式呼吁全社会关切传统文化、推动非遗保护工作。同时,他义卖个人绘画作品,创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
在多年的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冯骥才先生还为其主持的各项大型文化抢救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所出版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唐卡文化档案》《中国剪纸艺术集成》《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等文化档案和“中国口头文学数据库”,对我国留存、展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出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责任、使命与担当,冯先生向国家提出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将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等政协提案,提出非遗的抢救和普查、传统村落保护等建议,都得到国家层面的采纳与践行。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冯骥才先生开始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以下简称“非遗学”)新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非遗”的概念,是自本世纪初,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确立逐渐为国人所知。当时,我国学者向云驹先生撰写了关于非遗的第一本书——《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旨在向国人介绍非遗的性质、本质、特征、重要性、整体与逻辑,以及相关知识等。冯骥才先生应邀为该书写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学科理论的创建上说,这是平地起楼。它无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还是民间文化的田野普查与整理,都是必要和重要的理论支持。而其本身已具有文化遗产学的骨架与气象了。”
在序中,冯骥才先生基于一种学术的敏感有了“非遗学”的概念。这无疑是一种新的遗产观,可以支撑起一片全新的学科景象。而这景象,在蓬勃发展的非遗事业中愈来愈清晰。自上世纪末至今二十余年间,经过政府与学界、文化工作者及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将中华大地上规模浩大、灿烂纷繁的非遗项目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国家级非遗超过1500项,政府四级名录(国家、省、市、县)超过10万项,国家级传统村落6819个。我国列入世界非遗名录者达到四十余项,居世界首位。
但正如冯骥才先生在书中所说:“列入名录不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结束,而是保护工作的开始”。目前列入文化遗产的很多项目没有严格、专业和科学的保护。建立科学、全面的非遗保护理念、规则、方法,建立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家非遗保护事业的急需,也是文化事业上的急需。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切进入科学保护的新阶段。因此,“非遗学”的提出,已不再是学术的狂想,而是学术的必然。
在《非遗学原理》一书中,冯骥才先生系统地梳理非遗学科的缘起、使命、立场、特征、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竖立起非遗学的框架,阐述非遗学的独立性和学术本质,从元理论层面勾勒出非遗学独特的学科样貌,并为这一新学科的研究、实践方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原则。
“民俗学注重民俗事象的过去,非遗学注重非遗活生生的现在……非遗学是为了非遗生命的存续以及文化命脉的延续。”在《非遗学原理》一书中,冯先生论述了非遗学不同于民俗学、民艺学等相关学科的独立性,阐释了它不依附于其他学科,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的必然和必要性。他认为,非遗学本质是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其研究对象是活态的、动态的民间文化,其性质和内涵是跨学科的。
此外,冯先生还结合自身二十余年非遗实践与思考,阐释非遗的地域代表性、美学价值等关键命题,对非遗的视觉调查记录方法、非遗博物馆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思索与论述,同时也对非遗学的学术空白、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研究论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为非遗学立言与立论》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