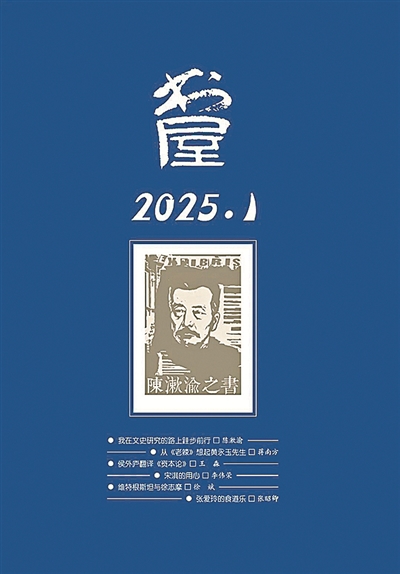
最新一期《书屋》杂志中的“书屋讲坛”介绍了在文史研究路上前行的陈漱渝先生。
陈漱渝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196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当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1976年调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后出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等职。期间先后参与《鲁迅全集》1981年版日记部分的注释定稿和2005年版的编注,《郭沫若日记》1982年版日记部分的注释,《鲁迅年谱》四卷本的编纂,《鲁迅大辞典》2009年版的撰稿,《鲁迅手稿全集》2021年版的编审。他个人出版的专著和文集有二十多种,其中《搏击暗夜:鲁迅传》被评为“2016年三十种好书”之一及同年“大众喜爱的五十种图书”之一。为青少年撰写的普及性鲁迅传记《民族魂》经不断修订,被不同出版社再版五六次。此外,他还从事宋庆龄、丁玲、胡适等人的研究,推出了相关研究专著。
陈漱渝先生自评:“此生的主要工作是鲁迅研究,而研究的重点确实是史料。”有关鲁迅的史料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认为,鲁迅史料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鲁迅研究的新史料也时有发现。
“什么叫新史料,或谓珍稀史料?当然是前人不了解或未引起应有重视的史料。要发现新史料,首先必须对课题的前期研究状况有所了解,越熟悉越好。”陈先生研究鲁迅之前,就利用了一些工具书,比如《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之类,这属于目录学范畴的知识。下了这番功夫才掌握了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知道哪些材料已经充实,哪些地方还有可以填补的空白,也就是所谓学术生长点。
陈先生认为,史料收集首先是文献资料。珍贵史料多采自珍稀刊物。当然,真正的史料研究不能单靠珍本秘籍。从一般人读到的书刊中发现一般人看不出的问题,才能显出研究者的功力。此外,口述史和日记、信札中也有不少真实而鲜活的资料,但因为这类资料主观性比较强,难免存在“误、隐、伪”的情况,需认真进行鉴别。“误”就是记忆有误,属于“无意失真”。“隐”是出于不同的主客观原因,没有将情况全盘托出,有遮掩性。“伪”指的是存心制造虚假信息。故而研究文献资料,需要具备一些文献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乃至笔名研究等等。
做史料工作如何才能成功?陈先生将其归结为一个“韧”字。俗话说,不怕慢、只怕站,搞史料研究比搞创作和探讨理论相对简单一点,关键在于锲而不舍。
(《在文史研究路上前行的陈漱渝》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