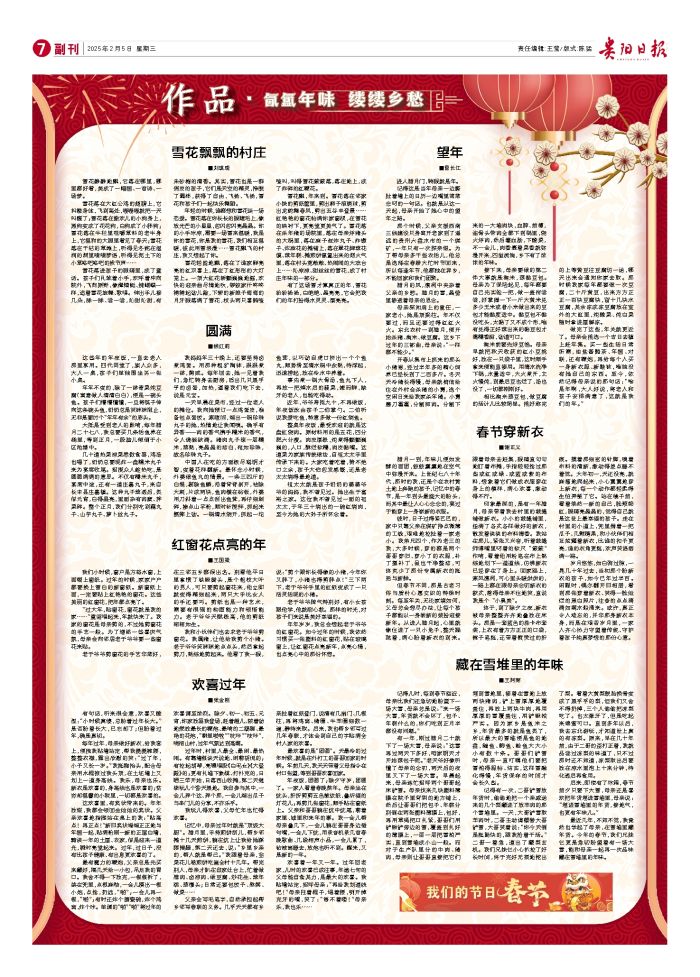■张金刚
有句话,听来很会意,欢喜又酸涩:“小时候真傻,总盼着过年长大。”是否盼着长大,已忘却了;但盼着过年,确是真切。
每年过年,母亲做好新衣,给我套上,便拽我贴墙站定,帮我提提裤腰,整整衣襟,露出欣慰的笑:“过了年,小子又长一岁。”我挺胸抬头,配合母亲用木棍掠过我头顶,在土坯墙上又划上一道身高线。我乐,母亲也乐。新衣是欢喜的,身高线也是欢喜的;贫穷却温馨的小院里,一切都是欢喜的。
这欢喜里,有奖状带来的。年年放假,我都会领回金灿灿的奖状。父亲欢喜地指挥站在桌上的我:“贴高点!再正点!”新旧奖状端端正正地与年画一起,贴满粉刷一新的正屋白墙,黯淡一年的土屋、农家,似是迎来一道光,瞬时亮堂起来。过年,过日子,没有比孩子健康、有出息更欢喜的了。
最有魔力的鞭炮,父亲总是先买来藏好,隔几天给一小包,吊足我的胃口。我舍不得一下放完,一根根拆了,装在兜里,点根麻秸,一会儿摸出一根小炮,点捻,扔远,“啪”;一会儿再一根,“啪”;有时还炸个搪瓷碗,炸个鸡窝,炸个冰。单调的“啪”“啪”将过年的欢喜调至浓烈。除夕、初一、初五、元宵,你家放罢我登场,赶着趟儿、较着劲地燃放最长的鞭炮、最响的二踢脚、最艳的花炮,“噼里啪啦”“吭咔”“吱咔”,响彻山村,过年气氛达到高潮。
过年时,村里人最全、最闲、最热闹。有靠墙根谈天说地、闲聊胡侃的;有拉起胡琴,亮嗓唱段《白毛女》《大登殿》的;更有扎堆下象棋、打扑克的,日晒三竿开始,日落西山收摊,第二天继续玩儿个昏天黑地。我自参与其中,一会儿弄个这、弄个那,一会儿端出瓜子与串门儿的分享,不亦乐乎。
我玩儿得欢喜,父母忙年也忙得欢喜。
记忆中,母亲过年时就是“顶级大厨”。腊月里,手持煎饼刮儿,帮乡邻摊十几天煎饼,躺在炕上让我给她踩腰捶腿,第二天还去,说:“乡里乡亲的,帮人就是帮己。”我跟着母亲,韭菜花儿卷煎饼吃遍全村十几年。帮完别人,母亲才趴在自家灶台上,忙着做腊肉、卤凉肉、做豆腐、炒花生、蒸年糕、蒸馒头;日常还要包饺子、熬粥、做菜……
父亲会写毛笔字,自然承担起帮乡邻写春联的义务。几乎天天都有乡亲扯着红纸登门,说清有几扇门、几根柱,再将鸡窝、猪圈、牛羊圈细数一遍,静待来取。后来,我也帮乡邻写过几年春联,才体会到自己的字贴满全村人家的欢喜。
最欢喜的是“团圆”。天最冷的过年时候,就是在外打工的哥哥回家的时候。年前几天,我天天带着父母指令在村口张望,等到哥哥欢喜回家。
年夜饭,团圆了;除夕守岁,团圆了。一家人看着春晚熬年。母亲坐在炕头,折折剪剪五色皱纹纸,叠祈福的灯花儿;再剪几张窗花,顺手贴在窗纸上。父亲和哥哥躺在炕中炕尾,聊着家里、城里和来年的事。我一会儿帮母亲叠几下,一会儿躺在哥哥身边插句嘴,一会儿下炕,用录音机录几首春晚歌曲、几段相声小品,一会儿累了,钻被窝睡去,放炮也听不到。醒来,又是新的一年。
欢喜着一年又一年。过年回老家,儿时的欢喜已成往事,年逾七旬的父母能自食其力,是最大的欢喜。我贴墙站定,招呼母亲:“再给我划道线吧!”母亲拄着棍子,塌着腰,咧开掉完牙的嘴,笑了:“够不着喽!”母亲乐,我也乐……
(《欢喜过年》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