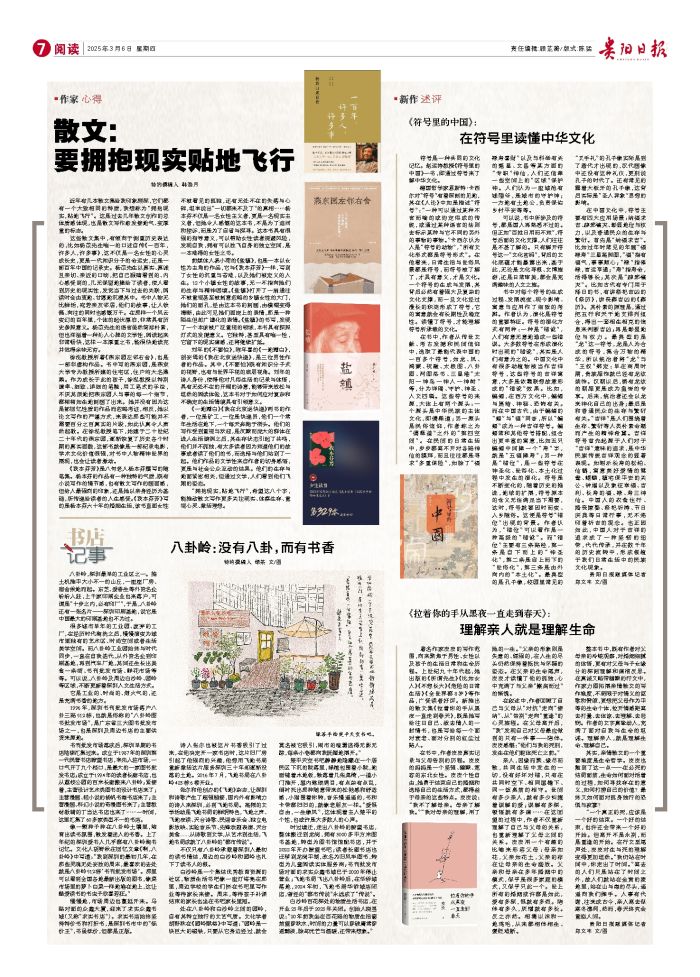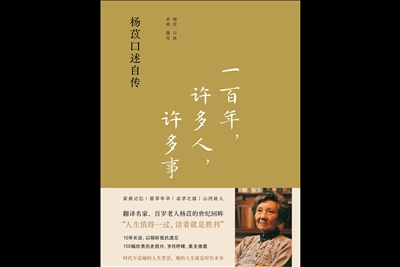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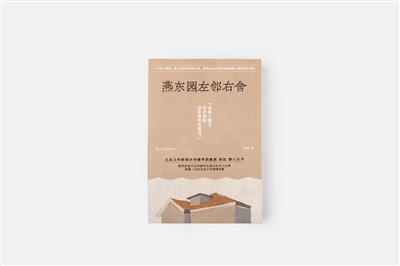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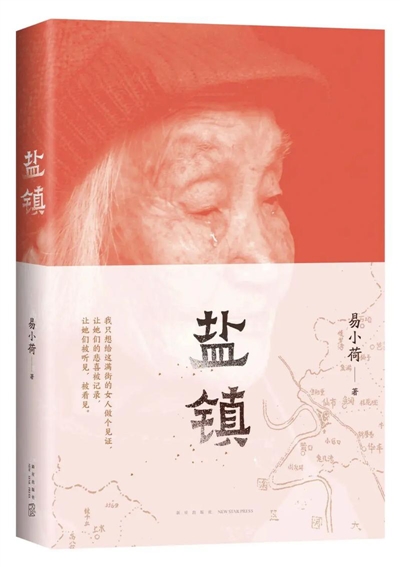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近年有几本散文集给我印象颇深,它们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特质,我想称为“拥抱现实,贴地飞行”。这是过去几年散文创作的总体质感体现,也是散文写作愈发接地气、变厚重的标志。
这些散文集中,有倾向于侧重历史表达的,比如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不仅是一名女性的心灵成长史,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还是一部百年中国的记录史。杨苡先生以真实、真诚且亲切、亲近的口吻,把自己眼睛看到的、内心感受到的,几无保留地捧给了读者,使人看到历史的现实性,发觉当下与过去的关联,阅读时会由衷地、甘愿地沉浸其中。书中人物无比鲜活,宛若亲友邻居,他们的故事,让人钦佩、向往的同时也感慨万千。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百年里,个体的起伏漂泊,非常具有历史参照意义。杨苡先生的语言虽然简洁朴素,但也洋溢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文学性,阅读起来非常畅快,这样一本厚重之书,能很快地读完并觉得余味无穷。
徐泓教授所著《燕东园左邻右舍》,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书中写的燕东园,是燕京大学专为教授所建的住宅区,住户均大名鼎鼎。作为成长于此的孩子,徐泓教授以特别谦卑、细致、详细的笔触,用工笔式的手法,不厌其烦地把燕东园人与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她并没有因为这是部回忆性质的作品而忽略考证,相反,她以论文写作的严谨方式,来表达那些可能并不需要百分之百真实的片段,如此认真令人肃然起敬。在徐泓教授笔下,始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燕东园,逐渐恢复了历史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这部书就像是一部纪录电影,学术文化价值很强,对书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现,也会让读者激动。
《我本芬芳》是八旬老人杨本芬撰写的随笔集。杨本芬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既有小说写作的情节感,也有散文写作的画面感,但给人最强烈的印象,还是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所传递给读者的人生感受。《我本芬芳》写的是杨本芬六十年的婚姻生活,该书直面女性不被看见的孤独,还有无处不在的失落与心碎,坦率说出“一切都来不及了”的真相……杨本芬不仅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但她令人感慨的这本书,不是为了追问和控诉,而是为了自省与探寻。这本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可以帮助女性读者规避风险,发现自我,拥有可以放飞自身的独立空间,是一本难得的女性之书。
前媒体人易小荷的《盐镇》,也是一本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它与《我本芬芳》一样,写到了女性的沉重与苦难,以及她们被定义的人生。12个小镇女性的故事,无一不指向她们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盐镇》打开了一扇通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刻意忽略的乡镇女性的大门,她们的面孔,经由这本书的刻画,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此可见她们面庞上的表情,那是一种陌生但却广谱化的表情。《盐镇》的书写,发现了一个本该被广泛重视的领域,本书具有探照灯式的发掘意义。它独特,甚至具有唯一性,它留下的现实痛感,还将继续扩延。
刘年的《不要怕》,陈年喜的《一地霜白》,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三位男性作者的作品。其中,《不要怕》既有知识分子式的视野,也有与世界平视的底层视角。刘年的诗人身份,使得他对凡俗生活的记录与体悟,具有无处不在的开阔的诗意,能够带来放松与坦然的阅读体验,这本书对于如何应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生活情境具有引领意义。
《一地霜白》《我在北京送快递》两书的作者,一位是矿工,一位是快递员,他们一个常年生活在地下,一个每天奔跑于街头。他们的写作受到重视与欢迎,是沉默而庞大的群体在进入生活漩涡之后,其生存状态引起了共鸣,他们并不孤独,有太多读者因为知道他们的故事或者读了他们的书,而选择与他们站到了一起。他们作品的文学性来自作者的切身感悟,更是与社会公众互动的结果。他们的生存与地面紧密相关,但通过文学,人们看到他们飞翔的姿态。
“拥抱现实,贴地飞行”,希望这八个字,能推动散文写作更多关注现实、体察生存、重视心灵、激活理想。
(《散文:要拥抱现实贴地飞行》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