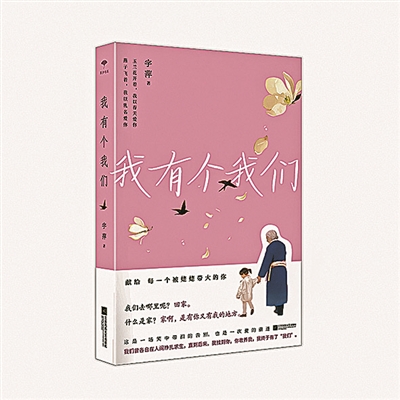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我有个我们》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乡书系”推出的一本新书,在书中,乌兰察布作为最为贴近“原乡”定义的一个地址出现,安徽和天津作为漂泊地与工作地出现,除此之外全书罕有其他地名,乌兰察布及其牧区,在作者宇萍笔下反复被描述,就像阿勒泰反复被李娟书写那样。
《我有个我们》是散文集,但完全可以当作一本具有强情节的小说来看:皖南某地,一位货郎婆婆(后来被作者称为姥姥),心疼福利院里一个名叫燕子的“小孩”(姥姥对作者一直的称呼),相差几十岁的她们,为了能更好地相依为命决定远走高飞。长大后的小孩,辞职从天津再次回到成长地。这两段经历的目的地,都是乌兰察布,她们经历过很多困难,但此地的“故乡”特征,还是给她们提供了“避难所”。
全书最具戏剧化的一个内核是,小孩有了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姥姥,并继承了姥姥在户口簿上的名字,姥姥去世后,“宇萍”这个名字具有了两个人的内涵,年轻的宇萍代替天上的宇萍继续认真地活着。天上的宇萍则以姥姥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年轻宇萍的生活当中——从许多年前走到一起,她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书中“双宇萍”的命名,展示了一种真实又非凡的文本创造能力,“宇萍”成为穿越生死的时光胶囊,承载了两代女性的生命密码。当年轻宇萍通过书写不断召唤“姥姥宇萍”时,读者看到的不仅是私人情感的流淌,更是“讲故事的人”对线性时间的抵抗——文学依然保有将瞬间淬炼为永恒的特权。
这样的故事,具有某种震撼性,它撬动一些在现代人观念中貌似已冰冻的情感深度链接意识,如春风驱赶严冬那样,给人以伸手可触般的暖意。
一个善良有爱、宽厚有加的老人,牵着一个瘦弱但却生命力旺盛的女孩,这个画面如同永恒的剪影,成为全书赖以完成的强大背景。在持续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发觉,姥姥已经取代所有地址与地点,成为作者的“精神原乡”。一个人可以渺小,但同样是这个人,也可以非常宏大,伟岸如故乡、开阔如大海、缤纷如四季……在书中,姥姥就是可以被写进“宏大叙事”中的人,她之于她所保护的人而言,就是整个世界,因为有她的存在,柔弱者有了一面可以向这个世界进击的盾牌,有了变得强大的机会与可能。
《我有个我们》分为三辑,分别讲述作者在生命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但有一股情感洪流贯穿其中,使得全书的分辑变得不再重要,这也是这本书看起来像是小说的原因。在不同的篇章中,姥姥的形象与话语,以及作者对记忆的拾掇与串联,可以帮助读者逐渐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开篇《第二十八春》中留下的讲述盲点,很有可能在后边《陌上花开》《暮秋之味》中得到填补,这带来了别样的阅读感受,读者与作者因此站在了同一个点位,让破碎重新完整,让不安得到安宁,把人生悲苦变成活着的喜悦,这本书阅读之外的附加值,是多元而丰富的。
这本书的出版,挣脱了“个人回忆录”的限定,预示着非虚构写作正在突破“记录”的单一维度,向“治愈”功能进化。同时,这部作品也提供了重新审视文学价值的契机,宇萍用时间与情感不断打磨的记忆书写,证明了文学不可替代的人文温度,书中被反复强调的那句“我有个我们”,更是一句诘问——“我”是否找到或者说真正拥有了“我们”?
(《看见两代女性的情感深度链接》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