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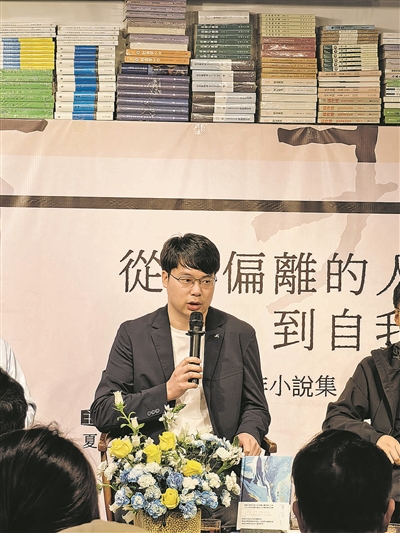
■人物名片 若非,毕节大方人,穿青人,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五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山花》《青年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曾获尹珍诗歌奖、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已出版长篇小说《花烬》、诗集《哑剧场》等作品八部。

分享会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毕节青年作家若非将近年来发表的12篇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书名《十二盏微光》,书中的12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地标:黔西北乌蒙山麓地区。12个中短篇作品既是微光也是十二面镜子,照见了自己、也照亮了生活在乌蒙山褶皱里的平凡人。该书发行不久即入选全国二十余家颇具影响力的图书出版单位联合发布的2025年4月文艺联合书单。
4月12日,贵阳市作协、市评论家协会在贵阳也闲书店举行新书分享会,著名作家、《南风》杂志主编冉正万,诗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思源,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团委员曹永相继发言,围绕《十二盏微光》的创作特色与青年写作、乡土写作等话题展开分享交流。分享会由省作协副主席、《南风》杂志副主编夏立楠主持。
“寻找”成就“传奇”
《十二盏微光》是若非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作者着眼于一个个平凡的乌蒙人,书写在时代变迁中的爱与忧愁、幸福与疼痛。其中有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文艺青年、深山里寻找自我的失意中年男子、善于倒立行走的乡村少年、治病疗心的乡村医生……他们流转在乡村、城镇、矿区等场所,职业身份各异——有守乡人、返乡人、异乡人,有出发者、归来者、守望者、来访者,但每一个人身上,无不深刻烙印着乌蒙的印记和时代的气息。
“书名叫《十二盏微光》,因为收入本书的十二篇小说都与我生长的乌蒙山这片土地有关。小说里,人物各有各的困境和悲苦,也各有各的坚强与执守,他们无论遭际如何,身上总能闪现出一丝微弱的亮光。”分享会上,若非结合自身的成长、生活和文学创作经历,分享了《十二盏微光》的创作初衷和心路历程。他说,“我长久地被这些人物身上的亮光感动着,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让更多人看见和感受到他们。同时也是寄希望于这样的一些写作和故事,观照乌蒙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隐秘的内心、山里山外的链接,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和人心的变化”。
“若非和其他本土作家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是从外部来打量生活的地方、由外向内地寻找,寻找故人、故地,寻找意义、寻找出路、寻找安放之地、寻找安身之所。这样的寻找基于小说,也基于人性和人心。”冉正万说。他以书中《溢补嗒启》《嘎依的来信》两篇小说为例阐释:若非巧妙地从北京、广州展开故事,用他者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熟悉的地方,顺理成章地呈现贵州元素,营造出朴实而又悬疑的氛围,让读者信以为真。作为一种技术,这增加了故事的传奇性,在如何吸引读者注意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叙事自觉,不如说是一种才华。“这种寻找本身有一种传奇性,很容易把读者拉进去,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写法。他的小说写乡村,写乡村的忧伤,也写到了这些平凡人为了活着的韧性和坚持。”冉正万说。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王祥夫也读到了“传奇”的味道。他在写给若非的新书序言《传奇到处流传》中写道:“读若非的小说,每一篇都像是与传奇无关,但读完之后,觉得一篇篇都是传奇,这一点,是若非与许多青年作家的不同之处,若非是乡间的或城市里的、是小风小雨却有大风大雨不可替代的情态。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从若非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纯粹的本色。”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读到了乌蒙深处的烟火人间。他评价:“若非善于捕捉乡野日常里的点滴光芒,他以强烈的关怀意识和悲悯意识,注目和书写着乌蒙山水间的平凡故事,既保持了隔岸冷望的姿态,又饱含身在其间的深情,行文间投射着温暖、朴实、自然、深情的肌理和神态。十二个生发于乡野的故事,如同十二株野草自然生长,以温暖微光照亮乌蒙深处爱与忧愁交织、温暖与疼痛共生的烟火人间。”
“细腻”“典雅”“民俗”的交响
题材之外,若非作品的风格也很有“辨识度”。
分享会上,张思源认为若非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文本内部氛围的构建能力,对文本内部的情感流动、意识流动,掌控能力都比较强;二是语言特别细腻,有大量的细节,绵密地推动。“(过于细腻)既是长处,也有可能会构成一种自我的限制。”张思源在认同的同时,也表达了担忧。
“若非迷恋细节,这让他的小说显得充盈、丰满。语言充满诗意,这与他曾经进行大量的诗歌写作有关系。”冉正万还看到了若非的多面性:作为贵州西部作家,他还擅长“暴力美学”运用,让快意恩仇成为情节本身,侠义、孤独、苍凉与贵州西部风景融为一体,读者情绪很容易被点燃;其次是青春气息,是我们经历过的逝去的青春。
省内名家李寂荡、肖江虹为该书作推荐。李寂荡认为,“若非擅长用‘河流’式的笔法,时而温柔时而激荡地描绘人的精神流向,让隐蔽的人性最终水落石出,绽放某种原初、真朴、终得救赎般的美感”。在肖江虹看来,“若非的写作纯粹、典雅,他不停在回溯中打捞,亦在打捞中回溯;波澜不惊下沟壑丛生,情感的生发与收束恰到好处。叙述绸缎般的丝滑与故事剪裁的立体形成了鲜明的个体印记。扎实、虔诚、睿智散落在作品的每一寸土地,持之以恒,将是无限的辽阔与宏大”。
“若非的小说里有一些民俗的内容。这些内容加入到小说的故事内核之中,或借用民俗、传说的外壳表现内心的东西,表现得非常精彩,也体现了地域作家的优势。”在同为毕节籍的青年作家曹永眼中,若非很勤奋,写作量和阅读量都很大,“这点从他的小说里能感受得到”。
互动阶段,若非针对观众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提问进行了回应。“写下个人,就是写下时代。”“写不了就读,读累了就写。”一句句金句式的回答,赢得阵阵掌声。
(《文学微光照见乌蒙山中人》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