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虫子》:
一个苦孩子的“昆虫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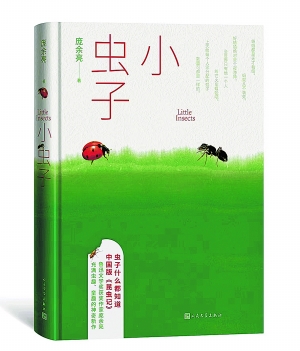
2022年,当过15年老师和5年记者的庞余亮凭借《小先生》一书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该书是作者根据自身从教经历所记录下的乡村孩子成长故事,充满了诗意、童趣与汉语的温润之美。评委称之为“续上了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贤善和性灵的传统文脉,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操场”。近日,“小先生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虫子》出版面世,讲述了一个苦孩子的“昆虫记”。
这里的“苦孩子”,就是童年时期的作家本人。庞余亮是江苏兴化人,自幼在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长大,他是父母的第十个孩子,也是家中最小的男孩,被一字不识的爹娘唤名“老害”。由于“僧多肉少”,从小过着苦日子的他记忆中最深的感受是饥饿与孤独。好在他也有自己的第一笔“财富”——虫子。他的童年和无穷无尽的虫子连接起来:春夏秋冬,出没在村庄的虫子是他的玩伴,是他的敌人,是他的玩具,是他的食物,也是他的零花钱。因为孤独和饥饿,他只能和蜻蜓、天牛、屎壳郎、蚂蚱、蚂蟥等小虫子为友、为敌。在与乡村虫子的拉锯战中,野蛮生长中的他体验到了世界的奥秘和生活的百味。长大以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笔“财富”——读书、写作。这样一来,“小虫子”和书上的字,成了命运派遣过来慰藉他这个苦孩子的糖果。
直接让这两笔“财富”产生关联的,是一本写小虫子的名著——法布尔的《昆虫记》。他买了3本《昆虫记》,1本在办公室,1本在床头柜上,1本在卫生间里,时刻可以在“枕上”“厕上”的空暇时间翻阅。无论多么烦恼、多么疲惫,打开这部书,他就感觉那些虫子争先恐后的,像精灵老师一般在敲记忆的黑板:“你把我们给忘了吗?”作家当然没有忘记,而是不断地在阅读、写作中,回望他和他的虫子单独相处的日子。
在书中,除了着重描绘瓢虫、蚂蚁、米象和蜜蜂这四种小虫子,作家还另外提及了近40种小虫子。但作家对虫子的描绘,并非研究的、科普的,而是生活的、有关生趣的人与身边自然共生互照之书。写的是性格,是对生活的态度,展现的是趣味,是欢喜,是爱与怕的共情。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但有丰富的触角和探究;没有苦痛的停留,只有世间万物相互照应的幽默。文字轻松活泼,延续了《小先生》的汉语之美,是庞余亮版的《昆虫记》,亦可作为《小先生》的童年前传,用含泪的微笑偿还了童年的所有神奇。
通过《小虫子》,庞余亮贡献了新鲜的、独特的、至今无解的昆虫知识,重新命名了童年和虫子。这本书是作家访问小虫子、访问童年、访问被忽略已久的自然和大地的作品。他认为,小虫子是打开童年、打开人生、打开自然奥秘的一把钥匙,和小虫子作朋友,不仅可以让孩子成为一个观察虫子、写出优秀的作文,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科学家,因为好奇心是创造世界的最强大动力,一个科学家没有好奇心不能成为科学家,要把孩子从手机和电子游戏中拔出来,靠什么拔?大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小虫子和大自然就有这个力量,小虫子和大自然真的能够拉大车,回到大自然中,和小虫子交朋友,真的可以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庞余亮的散文具有清新的诗意、神奇的魔力,像文气盈盈的翅膀,把读者载到时光深处的榆树河边、绿草地上。萤火虫好像一盏盏小灯笼,蛐蛐都是夜游神,洗干净的糖纸在阳光下就像新糖纸,母亲的“甜脸”会让整个屋子亮堂起来,螳螂、蜻蜓和知了都穿了乔其纱,上海的蜻蜓、北京的蜻蜓,都是从他们村庄飞过去的——这本他自己的《昆虫记》里,既有世间万物相互照应的幽默,又有浓郁亲情和自然生长的爱心,还有许多新鲜的独特的至今无解的昆虫知识,令人忍俊不禁,笑出眼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一个苦孩子的“昆虫记”》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 上一篇:李慈铭的京官生活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