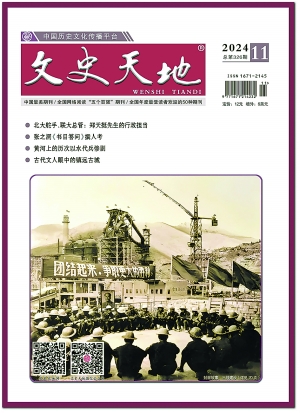
《文史天地》2024年11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刊发了郑天挺和刘文典两位先贤的文史类文章,两人在“西南联大”这一点上有可联系之处。
提及西南联大的成就和精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三位校长。三位校长的成绩固然为人称道,然就维系西南联大日常运转而言,三位校长只是名义上的“船长”,而郑天挺先生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当时,郑天挺以北大秘书长兼任联大总务长,全面负责北大及联大的财政、人事、庶务等琐碎日常工作。遇到重大事务,郑天挺才会请教梅贻琦、蒋梦麟两位校长,或者提请校常委会决议。文章还原了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经历。
文章写道,1933年开始,郑天挺开始了其18年北大秘书长的职责。按照北大当时的规章制度,秘书长负责全校行政总务,实际上就是北大“总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偌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北大“全校负责人均逃”,郑天挺独撑危局,一人掌管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的印信,扶倾救困,组织学校搬迁南下,这期间甚至遭到日方通缉。1938年3月抵达昆明后,因校舍不足,设备和人员均不能妥善安置,北大文学院暂迁滇南蒙自,郑天挺为此往返滇越铁路9次,投宿开远大东旅舍4次,其颠沛流离的艰辛和劳碌,外人简直不可想象。抗战胜利后,北大筹备复校,其时北大校长胡适也甚少过问学校事务,郑天挺又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复校事务。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郑天挺又独力承担起北大和平过渡的护校工作。1940年初至1946年,郑天挺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一职,承担所有具体的行政工作,如筹措办学经费、协调三校合作、平衡三校利益等。西南联大能办成国际一流的大学,不能忘记郑天挺先生的幕后之功。
1891年12月19日,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富商家庭。其父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刘文典6岁时,便请了私塾先生为儿子讲授四书五经,这为刘文典日后成长为一名国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到刘文典,人们会津津乐道于他的“狂”。所谓“狂”,一方面是指不畏强权,刚正不阿,不买当时国民党政要的账。一方面指对自身学问的自信。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开课近十门。因藏书都留在了北平,手边缺少必要的参考书,但他凭着超强的记忆力,把课程开成了联大十分叫座的课。他曾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算一个,冯友兰算一个,唐兰算半个,他本人算半个。这些“狂妄”之语其实当不得真,它们更像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性情之语。平心而论,在学问上超过刘文典的也确实不多,虽然他的话不无夸张。文章除了描述刘文典“狂”的一面,还特意写到了他对亡儿的念念不忘、对爱子的深爱,意在告知人们不能只知其“狂”的一面,他也有“柔”的一面。
(《西南联大的郑天挺和刘文典》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