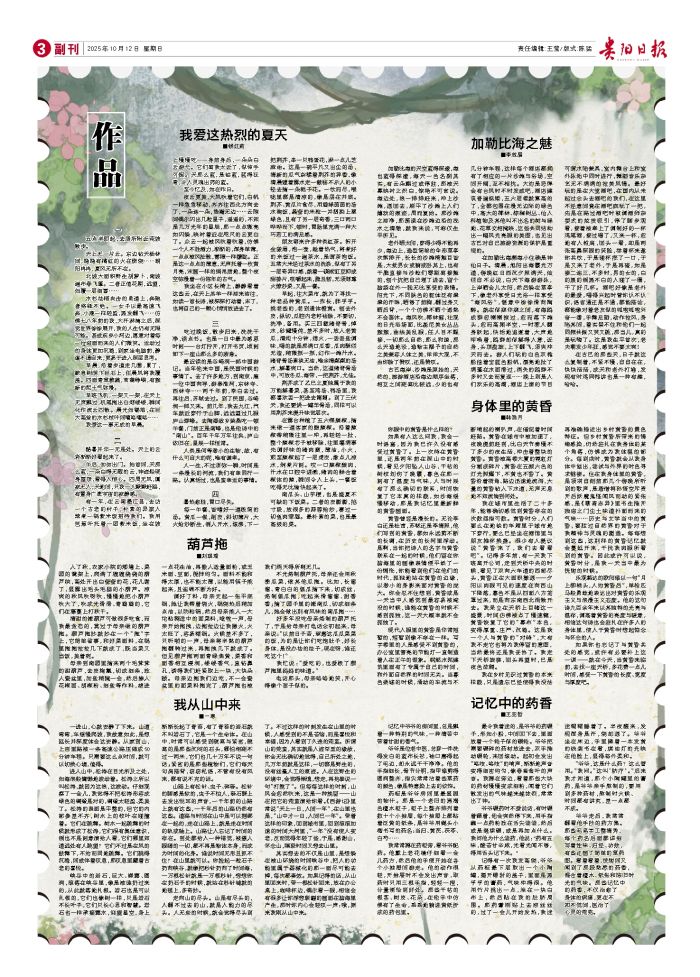■王亚哲
记忆中爷爷的房间里,总是飘着一种特别的气味,一种清苦中带着甘甜的香气。
爷爷是位老中医,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却永远干干净净。他的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指尖常常沾着些草药的颜色,像是特意染上去的纹饰。
药柜是爷爷房间里最显眼的物什。那是一个老旧的黑褐色檀木柜子,柜子上整齐排列着数十个小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泛黄的纸条,是爷爷用蝇头小楷书写的药名:当归、黄芪、茯苓、白芍……
我常常蹲在药柜旁,看爷爷配药。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一会儿药方,然后他的手便开始在各个小抽屉间游走。他的动作很轻,开抽屉时不会发出声音,取药时只用三根手指,轻轻一捏,分量便恰到好处。那些干枯的根茎、树皮、花朵,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乖乖地躺进黄纸折成的药包里。
最令我着迷的,是爷爷的药碾子,形如小船,中间凹下去,里面放着一个轮子似的碾轮。爷爷把需要碾碎的药材放进去,双手推动碾轮,来回滚动。起初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渐渐地声音变得细密均匀,像春蚕食叶的声音。我蹲在旁边,看着那些大块的药材慢慢变成细粉,闻着它们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烈,常常出了神。
爷爷碾药时不爱说话,有时碾着碾着,他会突然停下来,用手指蘸一点药粉放在舌尖尝尝,然后或是继续碾,或是再加点什么。我问他为什么尝药,他说:"药有五味,酸苦甘辛咸,光看光闻不够,得用舌头记下来。"
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爷爷从药柜最下层取出一个小陶罐,揭开蜡封的盖子,里面是黑乎乎的膏药,气味冲得很。他用竹片挑出一点,涂在一块白布上,然后贴在我的肚脐周围。那药膏刚贴上去凉丝丝的,过了一会儿开始发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浑身是汗,烧却退了。爷爷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在看,煤油灯的光映在他脸上,显得格外柔和。
“爷爷,这是什么药?这么管用。”我问。“这叫‘脐疗’。”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小陶罐里的膏药,是爷爷亲手熬制的,要用到多种药材,熬制时火候、时间都有讲究,差一点都不成。
爷爷走后,我常常翻看他手抄的药方集。那些毛笔字工整清秀,每个药名后面都详细写着性味、归经、功效,有些还画了简单的草药图。看着看着,恍惚间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药香,混合着檀木、纸张和陈旧时光的气味。那些记忆中的药香,不仅治愈了身体的病痛,更在不知不觉间,医治了心灵的荒芜。
(《记忆中的药香》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