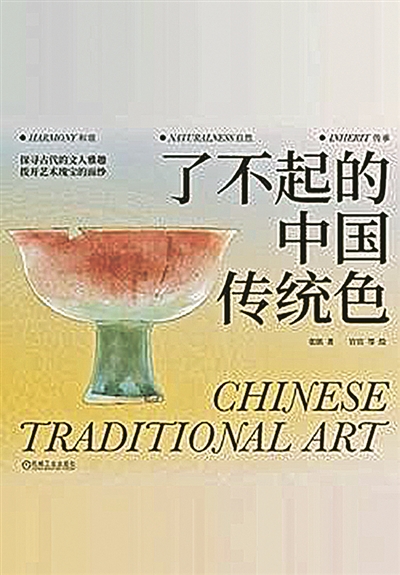
在中国文化的所有符号中,中国色既是国人定义颜色的方式,更是看待世间万象的眼光。学者张朋的新作《了不起的中国色》,详细阐述了每种中国传统色彩的来源、命名的故事以及其代表的文化内涵。
古代先民对于颜色的感知和理解是丰富而浪漫的: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出土的古老彩陶就有了朴素的颜色,呈现出赭红、黑、白几种颜色搭配的美丽图案;青铜时代,青铜器颜色最初是灿烂的金色,经过几千年的埋藏后,呈现出青绿、黑、蓝、银白、红褐等色;汉代黑与红被视为最高贵的颜色,人们认为大千世界的斑斓色彩都是从玄黑中生出来的,而红则是仙人的色彩,是吉祥与权力的象征,黑与红的绝美搭配在汉代漆器、壁画上尽显风范;至魏晋时,思想文化活跃,色彩展现出真实的、不加掩饰的自我风格。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以充满想象和浪漫的文学性色彩为主,那个时代的画家就注意到了固有色与光影变化对色彩的影响;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包容开放的强盛朝代,那个时代的色彩有典雅华贵、鲜艳明快的特征;到了宋代,颜色好像被淘洗一般沉静下来,以低饱和度的样貌呈现,淡雅、微妙的色彩变化和丰富的冷色调,将宋代人浑然天成、自然朴素的美学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明代崇尚儒家的道德思想,贵族的色彩风格华贵端庄,具有强烈、明丽的层次感。而棕色盛行于百姓中,并形成了诸多变化。明代的五彩瓷将中国瓷器发展转向了多色彩的维度;在清代,封建制度走到了顶端,这一时期的色彩繁华细腻,辉煌至极,体现中国古代工匠们顶级的工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色彩更加多元化、世俗化。
其实中国色之丰富,我们仅仅从颜色的千万种命名就可窥见一斑:有一些颜色来自某种直观的物象,比如竹青、栗壳、鱼肚白;有一些颜色来自天马行空的想象,比如人籁、水龙吟、迷楼灰;有一些颜色来自上古传说,比如吉量、朱草、蚩尤旗;有一些颜色来自某一种生活的动态或风俗行为,比如香炉紫烟、苍烟落照、葭灰。这众多与万物形态、人物心境、风俗传统、愿望与敬畏等相关的色彩词汇,正是中国传统色的奇妙之处,它们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了不起的中国传统色》一书从唐诗、宋词等的经典文学作品中选取内容,做了色彩分析,让我们从色彩视域下看到“有颜色”的古代文字。《诗经》对色彩的追求,是后世色彩审美的开端:“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可用深红色的绯红和朱砂色的彤表现新娘的美丽、古典和曼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则用米汤娇色表现春秋时期齐国公主庄姜的皮肤白皙细嫩,高雅而清丽的绝世之美。《诗经》开启的后世诗学传统,无不接续了这一颜色审美意识:王昌龄诗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中的磅礴之景,可用夕阳薄雾笼罩远山所现的暮山紫、清丽肃穆的千山翠来表现。而李白诗句“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中的浪漫之情,可用深蓝色的瑾瑜、浅蓝色的育阳染、碧蓝色的白青来表达。“满江红”既可以看作代表豪情壮志与英雄气概的词牌名,也能表现夕阳下,江水被覆满了火红浮萍的景色,它与肃穆的黑灰、藏蓝在一起,好像黑白山水画中的一片霞红,蕴含活力和生命力。“如梦令”是婉约系宋词的常用词牌名,词的内容总是带着少许甜美与忧伤,由此它是未经雕琢而自然美好的柔粉色,可用清丽温柔的藕色、热情温暖的岱赭来烘托。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传统色彩不仅多元,且有秩序。先秦时期,“五色体系”成形:东方属木,色青;南方属火,色红;西方属金,色白;北方属水,色黑;中央为土,色黄。颜色和时间、空间结合起来,又融入阴阳五行学说,由此形成了五方位、五元素、五色彩——这是古人眼中的世界。又因为青、红、金、白、黑是可以直接从大自然中提取的五原色,故而被视为正色;而用五原色相混而来的颜色被称为“间色”,依次原理形成了颜色的等级体系:正色贵,间色贱。
《了不起的中国传统色》一书还选取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诗词、中国画、壁画、建筑等,提取其中精彩的传统色,发掘它们最初的古意与来源,分析这些独特颜色的属性、各自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并给出具体的应用规则与方法。
另外,书中还介绍了中国传统色与众不同的分类和提取原料。与西方色彩最为不同的,就是中国传统色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灵巧的手工艺,是以中华大地上的植物、矿物、金属,甚至动物为提取原料。比如取自“蓝草”的花青,取自“茜草”的胭脂和取自“蓝铜矿”的石青、石绿等。同时,很多能够提取颜色的植物与矿物,还是中药的珍贵来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揭示中国色的“前世今生”》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